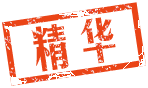|
|
本帖最后由 秦家女儿湘 于 2011-11-18 20:39 编辑
六奶奶印象
“跳拐拐,接奶奶,奶奶在屋里打草鞋……六奶奶,技术高,马鞍儿皮鞋当水瓢……”
那时的我们还是一帮小屁孩,放学后或者节假日总爱在一起耍,如迁徙的大雁,一会儿排着一字,一会儿团坐一块儿,顺口溜就出来了。有的是大人教的,有的则是伙伴间学的。叽叽喳喳的,也常惊得成团的麻雀叽叽喳喳扑棱着翅膀逃往林子里。
马鞍皮鞋就是山里人穿的一种齐脚颈的胶鞋,至于能不能当水瓢,我倒像个老学究一样还真试过,我拿它在场子边的水坑里往猪食桶里舀水。母亲看见了正色的说:“你在搞啥子啊?”哥哥随口便说开了:“刘奶奶,技术高,马鞍儿皮鞋当水瓢。”他们都笑了,我也得意的笑了。
至于六奶奶用没用马鞍皮鞋来舀过水,我们伙伴间也曾争论过这个问题。有人说不可能,也有人曾信誓旦旦说做过,自己的叔子伯爹舅舅姨妈亲眼见过云云,但我们从未见过。至于六奶奶其人,我努力起动大脑搜索引擎,似乎也只能找到几个不成形的片段,有的甚而还要加进自己一点想象才能成型。
六奶奶寡居,老伴六爷已先她十多年去世了。独自一人居住在一大片房子的一边,歪歪扭扭的一长间土坯房,土房被隔成三间,依次是厨房、睡房、搁粮食农具的房。几边的树齐刷刷往上长,伸长的树枝把六奶奶的房子遮去了多半边天,像要窥探啥秘密似的。我们小孩子从不去那里玩,阴森森的。
以我现在的眼光看,当年的六奶奶绝对是顶尖级大美女。既不是小芳型的,也不是黛玉型的,大概是李若彤型的,但似乎又不太贴切。那时她已八十多岁了,长年穿着船形的布鞋,走起路来没有老年人的那种蹒跚。也许是她的脚当年没有好好缠的缘故,比一般的老太太都要大。白鸡皮、鹤发。宛如后山上石缝中长出来的龙木,嶙峋而有精神。总之,六奶奶老而有品。据说,六奶奶有五个孩子,一女嫁得不远,但早逝,一儿子在外县当县长。其他的也都在外地,或工作或出嫁。总之,我从未见过。
我与六奶奶唯一的一次正面接触是在一年春节,姐夫姐姐抱着未满一岁的外甥去串门,走到六奶奶们那片屋场的场子上,外甥胸前挂的擦鼻涕的手绢忽然花蝴蝶般的飘落在地。过了丈把远姐姐就发现了,此时的六奶奶不知从何窜出,一把抓起小手绢。姐姐朝六奶奶那里望了望,正准备说什么,姐夫立马回看六奶奶一眼,朝姐姐会意的一笑,拉着姐姐走了。我这个跟屁虫,落后他们好几丈远,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当时的六奶奶,双手捧着手绢,放在脸前作擦鼻涕状。她盯着我,但迅即又恢复常态。那目光如电,把我想说的话一整句给囫囵击打到肚子里去了。那如电的目光,如我奶奶的,怕。奶奶去世前我守在她的床前,看着她目光忽然明了一下又黯淡张大着嘴巴到另一世界报到去了。于是好长时间我不敢走夜路,感觉奶奶在后面看我。六奶奶的不同,在我脑里。
六奶奶的形象在我心中明晰了又晦暗,晦暗了又明晰。好多年后,六奶奶终于以一个明晰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顺着我们这个村落,弯弯绕绕走过几座山,一座巍峨的大山脚下,一座气派的房子矗立在那里。青石砖砌成,四井口,绵延十几间,现在依稀可见痕迹,这儿就是六奶奶当年的娘家。多年前,娘家的后人拆除老房时,据说在一个屋角下挖出了几百银元。六奶奶应该是个大户人家出身,至于她为何嫁给当年贫穷的六爷,则有了不同的说法。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父亲雄赳赳气昂昂的从责任田里背回大背篓大背篓的苞谷,倒满了大半间堂屋。时令不等人,晚间,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矗在那苞谷山上,我们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剥去那苞谷的外壳。夜深了,为了驱赶瞌睡,父亲曾为我们讲过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一户地主,地主的女儿看上了他家的长工,不顾家人的反对,硬是嫁给了长工。新婚的晚上,新娘子那双娇嫩的手触到了长工的脚,嗔怒的说,看你真仔细,睡觉还把草鞋穿在脚上。新郎官连忙把脚躲开,不料,新娘的脚触到了新郎的手。新娘说,哎,看来你还真仔细,叫你别穿在脚上,你又把它拿手上了。
我很怀疑这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六奶奶和六爷。年轻的六爷一人种着从地主家租来的二三十亩地,做新郎官的六爷壮得像头牛,年轻的六爷定是夜夜春宵。而此时三奶奶一定是夜夜以泪洗面,套用一句广告词,恋人结婚了,新娘不是我。六奶奶和三奶奶是情敌,骨灰级的。她们俩斗了一辈子,骂了一辈子。骂来斗去,一前一后的从这个世面上消失了。 |
评分
-
查看全部评分
|